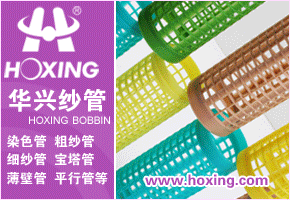梅新育:中美经贸争端升级 中国如何把握主动
最近几年,以美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为表现的全球经济失衡空前严重,中国则是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之一,是美方统计的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中美经贸争端有激化之势。
按中方统计,2006年对美贸易顺差1443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对美贸易顺差347亿美元。按美方统计,中国从2000年开始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2000~2006年对华贸易逆差分别为838亿美元、830亿美元、1031亿美元、1240亿美元、1620亿美元、2016亿美元和2325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为570亿美元;2006年和今年第一季度,对华贸易逆差分别占同期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28.4%、31.7%。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而然成为美国压缩经常项目逆差的重点;而在“美国贸易逆差根源在于中国不公正贸易行为”的基本前提假定下,贸易保护和压迫人民币升值又被许多美国人视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灵丹妙药,“敲打中国”成为美国某些势力乐此不疲的游戏。
随着民主党因中期选举获胜而把持国会山、华盛顿形成白宫与国会由两党分治格局,加之小布什已经因为伊拉克战争而深陷泥潭,为了赢得总统大选胜利,民主党议员们有着更强烈的动机要挟中期选举获胜余威而在一切可以发难的议题上“宜将剩勇追穷寇”,华盛顿的贸易反华风潮明显加剧,今年3月,美国国会两院贸易涉华提案竟有8个之多。
在此情势下,中国必须对今后持续的贸易争端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也不能单纯指望通过巨额采购大单来完全化解和应对。“上兵伐谋”,中国的“谋”又在哪里?
争端升级轨迹
美国对华贸易争端的主题覆盖面极为广泛,而且有日趋广泛之势,从早期的纺织品、服装,直到后来的农产品(21.90,0.00,0.00%)、反倾销、知识产权,再到这几年如火如荼的金融服务市场准入、人民币汇率安排等领域,大有无所不包之势。就总体而言,其发展趋势呈现出以下3个突出特点:
(一)争端商品产业层次日趋提高
由于中国外贸商品结构不断提高,美欧等发达国家对华贸易争端商品不断向高端发展,自是不足为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旨在发展自主先进制造业的努力正在遭受美国的狙击。
上世纪80年代以降,旨在选择主导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发展政策成为我国产业政策的主旋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除了少数旨在争夺世界科技前沿的领域之外,我国制定实施的大多数产业发展政策都带有浓郁的“进口替代”色彩,即使其所针对的产业属于典型的出口导向产业,产品出口比例甚高,我国相关产业发展政策的重心也是提高该产业投入品的国内增值率,实现该产品经济意义上的国产化。鉴于实施大约十年之久的“以市场换技术”方针实践结果与期望相差甚远,我国产业发展政策获得了新的强劲发展动力。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第(11)条指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任务,关键是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掌握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增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第(12)条比较详细地阐明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要点;第(27)条“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进一步提出,要“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继续发展加工贸易,着重提高产业层次和加工深度,增强国内配套能力,促进国内产业升级”。
然而,我国产业发展政策也有可能成为贸易争端的源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日,商品、资本、技术、信息和人员的洪流正将昔日彼此分割的各国市场日益紧密地联结成统一的世界市场,各国国内经济政策与其对外经贸的互动作用日益突出,更不用说那些本来就带有浓郁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政策了。贸易伙伴的反应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对其经济政策的影响就是一个突出范例。因此,各国在制订任何一项产业发展政策时,都不能不顾及该政策对其贸易伙伴的影响及其可能作出的反应。就我国而言,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我国产业发展政策所使用的政策工具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和调整,许多昔日常用的政策工具(如禁止性关税、进口计划等)已经取消,或正在逐步取消过程之中;而这些调整又有不少是应贸易伙伴要求、经过艰巨复杂的博弈而最终决定实行的。回顾我国入世谈判过程和入世协议,比较1994年3月颁布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与2004年颁布实施的新《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就可以发现这一点。由于发达国家与我国产业发展政策的利害冲突最为显著,从而决定了我国产业发展政策有很高的几率成为美欧贸易政策攻击的目标。正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狙击下,近年我国已有多项产业发展政策被迫推迟实施,如宽带无线局域网(WLAN)中国WAPI标准因为与美国IEEE 802.11i标准的争端而推迟实施、软件采购政策推迟实施,等等。2003~2004年中美半导体税制争端、2006年中国汽车零部件贸易争端等也颇为引人注目。预计当中国的自主创新大飞机等战略工业相继投入实际运作之后,也将面临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掣肘。
(二)从单个商品争端上升到整个经济结构层面
中国已经深刻地融入了全球经济,中国的廉价商品出口和低息融资对美欧实现近10年来的无通货膨胀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经济走势、贸易政策对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内的国际经济影响正日益上升。在这种背景下,正如当年美国对日贸易争端从单个商品争端上升到美日经济结构谈判一样,美国对华经贸争端已经从单个商品争端上升到整个经济结构层面,人民币汇率、中国国民储蓄率和消费率之争都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扩大国内消费(这也是主要贸易伙伴所要求的),国内工资水平提高,出口商品成本趋向提高,可能会加大美欧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这在去年的欧洲国家已经有所显现。2006年,继4月上扬2%之后,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于5月同比再度上扬2.2%,创7个月来最高点,通货膨胀压力显著上升。而且,英国当时的通货膨胀压力带有明显的外部输入特征。在截至2006年4月为止的12个月中,英国基本进口商品(除能源和轮船、飞机等价格波动大的商品之外)价格上涨3.6%,是1996年1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其中,来自欧盟国家的进口商品价格涨幅为2.1%,来自非欧盟国家的商品价格涨幅则高达6.2%,英格兰银行行长默文·金将英国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与中国出口成本上升联系起来了。我们需要分析这一趋势对贸易伙伴国内经济稳定的影响,贸易伙伴可能会因此与我们产生何种新的争端。
(三)更加倚重世贸等多边机制
鉴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对于中国对外经贸平稳持续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业已加入世贸组织,并相应承担了诸多义务;在对华贸易争端压力加大的同时,美国处理争端的策略日益强调利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去年2月14日,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中国入世以来第一份全面评估对华贸易关系的报告——《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U.S. Trade Relations: Entering a New Phase of Greater Accountability and Enforcement,下文简称《报告》),其中多处提及要确保中国履行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义务。该《报告》中提出的最引人注目措施之一是组建对华执法特别工作组,并规定该工作组将集中力量准备、处理世贸组织潜在涉华案件。
美国的这一新策略很快便投入实践。本来,从2002年1月1日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至去年,除2002年与欧盟、日本等国家/地区共同向世贸组织起诉美国的钢铁保障措施之外,我国不仅未曾单独提出任何诉讼,就是对其它国家提出的起诉威胁也通常是通过双边磋商加以化解,没有一起对华起诉威胁最终正式进入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但《报告》发布不过一个半月,去年3月30日,美国就和欧盟共同向世贸组织投诉我国《构成整车特征的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办法》,加拿大随后加入。这场争端发生后,虽然中方努力争取通过双边磋商途径解决,并主动推迟实施这项管理办法,欧盟、美国和加拿大最终仍然向世贸组织要求设立专家组,正式进入争端解决程序。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去年10月,美国俄亥俄州新页(NewPage)纸业公司要求美国政府对中国纸业企业进行反补贴调查,并对从中国进口的铜版纸课征近100%的反倾销税,挑起了对华铜版纸反补贴争端;今年2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施瓦布宣布,美国已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指责中国为国内制造商提供补贴以刺激钢铁等行业的出口。美国时间3月30日,美国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Carlos Gutierrez)宣布对中国适用反补贴法,并发布向从中国进口的铜版纸征收反补贴税的初裁决定,标志着美国不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商品征收反补贴税的判例正式终结,开创了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之先河。
当地时间4月9日,施瓦布再次宣布,美国将向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起诉中国知识产权(主要是版权和商标)保护和出版物(书籍、音乐和视听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不仅美国行政部门,就是国会山挑起对华争端时也体现出了这种转变。今年6月,舒默、格雷厄姆、鲍卡斯、格拉斯利4个美国参议员公布了所谓应对“中国等国家不公平低估货币”的法案,其中就煞费苦心把“货币低估”与世贸组织规则联系起来,并强调通过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解决争端。
美国:“先声夺人”的舆论引导机制
在任何谈判中,当事方都需要通过引导国内外舆论形成对自己有利的舆论环境,这样对外有助于赢得谈判主动权,对内则有助于凝聚国民共识,赢得稳固的国内支持。在通过舆论引导机制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推动实现自己的贸易谈判目标方面,美欧(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最为成功。其舆论引导机制最成功之处在于其重心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引导舆论。他们通过定期发布宏观经济和对外经贸统计数据、各类对外经贸报告(贸易壁垒报告、国别贸易报告),以及不定期的贸易听证会等方式,向国内外舆论界和社会公众灌输他们的立场观点,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抢占贸易谈判的舆论主动权。
在策略运用方面,在处理争端事务时,他们常常向贸易谈判对手设置“指责—否认”陷阱。所谓“指责—否认”陷阱就是不管一件事情是否真的违反公认的道德准则,也不管对手是否真的做过这些事情,抢先声称对方做了这件事情,并将此作为一种罪恶大声指责。如果对方不分析他的荒谬之处,只是马上反驳说自己没有做这件事情,这等于是对方已经潜在地认同了他主张的规则、他主张的价值观。
举个也许有点荒谬色彩的例子。假设甲和乙处于某种对立状态,甲希望乙接受他的规则,他的价值观,于是便大声指责乙:“你看你!居然咳嗽!”,乙如果立即大声疾呼否认:“我没有!我没有!我从来就不咳嗽!甲是造谣!是诬蔑我!”在这种否认声中,乙实际上等于潜在地认同了甲的规则,即“咳嗽属于不道德行为”。这样,有可能乙确实没有咳嗽,甲其实也不在乎乙是否真的咳嗽了,他只不过要在甲和乙之间建立一种潜在的规则:“咳嗽是不道德的”,这样就成功地对乙实施了控制。要摆脱甲的控制,乙的正确方法应当是反唇相讥:“问题的关键不是做没做这种事,而是这种事究竟是否属于不道德行为。如果不属于不道德,那么做不做这种事是我的自由,我也许将来会做这样的事,也许不会,你管不着。”
另外一种策略是有人唱红脸、有人唱白脸的“双簧”策略,一方提出比较极端、因而注定不可能实施的贸易报复方案,另一方则表现得相对温和,提出事实上是他们真实意图的方案,以此诱导对手接受。如美国在处理对华经贸争端中,国会和行政部门事实上就是如此分工的。当前,由于对中国相对较为了解,现任财政部长亨利·鲍尔森更倾向于同中国展开理性的协商,相信这是增进美国利益的更好途径;也正由于他的上述中国背景,在美国最高决策层眼里,他是与我国开展温和对话的合适人选,但无论是由鲍尔森还是其他任何人来执行这个使命,美国都不可能因此而取消查尔斯·舒默之流对中国大叫大嚷的角色。
在向贸易伙伴给予援助、单方面市场开放等优惠待遇时,他们通常奉行“大礼包策略”,即将多项贸易措施组合成一个综合性的经贸协定,当作是给贸易伙伴的一个“大礼包”,这样能够扩大宣传效果。
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掌握国际舆论的主导权,特别是国际媒体界的“盎格鲁-萨克逊霸权”几乎有无远弗届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舆论引导方面处于相对劣势。在舆论引导机制建设方面,发展中国家总体上没有多少超出发达国家的地方;而在策略运用方面,发展中国家仍有其独到之处,如运用人道主义、发展等更高层次的价值观来遏制发达国家的不合理要求等,最典型的成功案例莫过于南非、巴西政府与西方大制药商艾滋病药品专利权诉讼案,南非、巴西、印度等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社会力量成功地把那些西方大制药商推上了全世界的道德审判台,最终在2001年11月世贸组织多哈部长级会议胜利通过《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宣言》,明确宣布执行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不能妨碍穷国获得必要的药品供给,巴西将此列为在多哈回合中的两大胜利之一,确非言过其实。
中国的策略选择
中美经贸争端的是非曲直,在此无需赘言。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全程,中国都将面临来自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争端压力;文化背景和政治制度迥异将进一步加大这种压力。因此,应对这种贸易争端压力是中国的长期任务。在长期的经贸争端和对外谈判过程中,中方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今后需要在贸易谈判策略(包括谈判渠道选择策略、新规则策略、反贸易保护主义同盟军策略等)、预测/技术支持机制、舆论引导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特别是需要加强预测/技术支持机制,改事发之后的被动应对为防患于未然的预警措施。
就总体而言,尽管我国需要适度提高强硬姿态的比例,但毕竟贸易关系破裂和双边经贸环境动荡不安不是我们对中美和中欧经贸关系的期望,我们还是应当力求尽可能多地通过经济协商解决问题,防止双边意见分歧激化成为争端,为中美双边企业和员工创造尽可能稳定的商业环境。
从更高的层次上看,经济社会化决定了现代经济运行已经无法离开宏观调控,国际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经济政策溢出效应日益显著进一步决定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不可缺少。随着中美双边经贸不断扩大和深化,尽管中美经济协调与其它双边经济协调相比的突出特点就是贸易争端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但贸易争端因其高度不确定性而对正常经贸环境构成了巨大干扰,成为它作为一种广义经济政策协调方式的致命缺陷,因而在正常无争端状态下进行的机制化的经济政策协调渠道必然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从1979年2、3月间中美两国财政部长在北京就成立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China-U.S.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达成正式协议,成为中美双边经济协调机制之滥觞;到1983年建立中国外经贸部与美国商务部、贸易代表署对口的中美商业贸易联合委员会(简称中美商贸联委会,Sino-U.S.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再到2003年建立中美经济发展与改革对话(China-U.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 Dialogue)机制,中美双边经济协调覆盖面日益广泛,协调不断深入,协调议题从当初的单个商品贸易争端发展到了讨论调整整个经济结构。2006年建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更是覆盖面空前广泛,其议题不仅覆盖了两国之间几乎所有经济领域的问题,而且覆盖了诸如环境之类传统意义上的非经济目标。我们需要进一步挖掘这一对话机制的效力。
就结束不久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而言,双方都确认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着眼于长期战略目标的原则,但在任何谈判/对话机制中,当事双方就近期问题作出一定的具体安排,对于取得国内支持、保证谈判/对话机制平稳持续发展都极为重要,对于互利之中有摩擦的当事双方,取得这种具体成果的重要性尤其重要。正因为如此,此次对话前夕,鲍尔森对媒体放话,强调需要取得一些“路标”(signpost)式的成果,由于涉及利益重新划分,要达成这种具体成果又注定是艰难的。在中国对外经贸实践中,我们已经无数次见到这种情况:贸易伙伴内部各方在原则上一致赞同发展对华经贸,一旦涉及具体议题便意见纷繁歧异。要突破这种局面,在最大程度降低副作用的前提下取得最大限度的实际进展,双方就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尽可能寻找双方国内都赞成的措施;对于需要某一方国内作出较大调整努力,或是对某一方潜藏较大冲击的措施,则寻找潜在冲击风险最低的合适时机。
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中美之间更复杂的双边经贸关系了:它一经起步就发展迅猛并且不断显示着持续深入发展的深厚潜力,但起步伊始双方就摩擦频仍;它让双方都从中受益非浅并成为维系双边关系的最重要纽带之一,但双方却又相互猜忌;……作为发展最迅速的新兴大国与现任唯一超级大国,无论是对于当事国人民及其政府,还是对于整个世界;无论是出于经济利益,还是为了增进安全;磨合中美关系、协调两国经济政策都非常重要,但这种协调又必定是艰难的,甚至不无痛苦,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