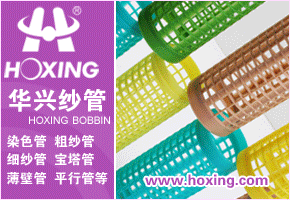艾得莱斯:此锦只应天上有(图)
西方的学者们把中国古代凡是进行丝绸贸易所能达到的地区,统称“丝绸之路”。然而,这曾牵动着东西方来往商人命运的丝绸并非只来自中国的中原一带。在古道上年复一年西行的丝绸,也曾悄然改变它本初的容颜,浸染了更多新鲜神秘的元素。地处丝路南道要冲的于阗(音“tian”,今新疆和田地区)就盛产一种著名的丝绸—艾得莱斯绸。
正如其诞生地一样,“艾得莱斯绸”吸聚东西方精华,闪烁着有别于中原丝绸的异样光彩。那么,桑蚕何以能落户于阗?古代中原不传之秘的丝绸纺织术又何以能在此地勃然传播?艾得莱斯绸到底魅力何在?桑蚕何以落户于阗?古代中原不传之秘的丝绸纺织术又何以能在于阗勃然传播?除了那则传丝公主的传说依然鲜活,艾得莱斯绸的来历依然是一个难解之谜。“传丝公主”将丝绸带入于阗?《新唐书·西域传》曾称于阗之人“工纺织”,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也有过类似的评价。而今,这些有着赞许成分的话语依然是那么恰如其分。和田以艾得莱斯绸为代表的丝绸文化仿佛是一个永恒谜题,吸引着人们无休止地去追问去破解。
“艾得莱斯”即维吾尔语“扎染绸”之意。新疆的和田地区,即古之于阗国所在,作为陆地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枢纽,正是艾得莱斯绸扎根、生长、繁盛之地。每当看到色彩艳丽、对比鲜明的艾得莱斯绸,一种裹着大漠风尘的异域情调就会扑面而来。环顾艾得莱斯绸的周边,花帽、胡旋舞、手鼓、热瓦甫,洋葱、孜然、葡萄、哈密瓜,一切似乎都与中原风物迥然而异。可是,只要我们略加考察就会发现,艾得莱斯绸的根仍然扎在中原大地。
从某种意义上说,“丝绸”二字便意味着中国。西方人先识丝绸,方知中国。西方人称丝织物为塞尔基(Serge),称中国为塞里加(Serica),称中国人为塞里斯(Seres)。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西方学者并不清楚丝绸的来龙去脉。有人以为丝绸是从树上长出来的,有人以为吐丝的蚕跟蜘蛛一样长着8只脚,要用稷养上4年、青芦养上5年才会从肚子里吐出丝来。然而,于阗的塞种人却很早就得悉了丝绸的真实秘密。古时候,漫漫丝绸古路虽然商旅往来频繁,交易活络,但一切有关丝绸的核心秘密—蚕桑技术却是被严加封锁,决不允许被从中原帝国带出关的。那么,中原蚕桑技术又是怎样传入西域的于阗国的呢?从下面这个故事里,我们或许可略见其端倪。
于阗王曾娶一位来自东国(也有书说是中国)的公主为后。在迎娶公主时,于阗国的使者暗中请求公主想法把桑蚕养殖技术带来,这样将来于阗国民就可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了。公主将这个请求暗记于心,下嫁之时,她偷偷把桑蚕种子藏在帽絮中,一路骗过关防。这样,才把养蚕制丝的方法传到了于阗。从此以后,于阗“桑树连荫”,本地居民方可自制丝绸。“传丝公主”的故事原来只见于古老的《大唐西域记》之中,可没想到在近现代的考古挖掘中它居然得到了验证。考古学者曾在和田东北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块8世纪的木板画,上面描绘着一位中国公主戴着一顶大帽子,一个侍女正用手指着它。研究者都认为,这里所画的正是那位传播养蚕制丝方法的丝绸女神。传说归传说,我们仍需要事实来验证。
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发掘出大批记载西域丝织生产的汉文文书。另外,在尼雅古城出土的距今至少2000年的丝绸碎片,竟和今天的艾得莱斯绸制作工艺完全相同。蚕、桑树和手工纺织工具残件,的确证明了艾得莱斯绸拥有异常古老的历史。桑蚕何以落户于阗?古代中原不传之秘的丝绸纺织术又何以能在于阗勃然传播?除了那则传丝公主的传说依然鲜活,艾得莱斯绸的来历依然是一个难解之谜。美丽艾绸的“硬件”与“软件”大凡一种声名久远的好物件,其诞生与繁盛总是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艾绸亦是如此。和田养蚕业之盛,也与当地的自然条件有关。和田气候温和,阳光充足,雪水丰沛。特别是这里春天来得较早,气温提升快,夏季气温稳定而不过高,对于栽桑育蚕很适宜。据一位养蚕专家说,仅和田一地的现有桑树数目,就达到江苏、浙江两省之和。制作出优良的艾得莱斯绸,光有桑蚕这些“硬件”还不够,还必须有“软件”—即过硬的技术手段,最主要的即扎染技艺。扎染又称扎缬、绞缬或染缬。中国染缬艺术的形成条件早在周代以前便已具备,在秦汉时期开始流行。到了六朝时代,绞缬已经是“贵贱皆服之”,可见当时应用已很普遍。
直到今天,在大理白族地区、海南黎族地区、四川自贡地区仍然保留了古代的扎染技术。中原的扎染工艺也是一路西传。解放后从新疆阿斯塔那地区先后发掘出土六朝时代的红色白点绞缬绢、绛色白点绞缬绢,都是重要证据。在具体工艺上,直到今天,和田农民制作艾绸仍然用原始手工操作工艺,与海南黎族使用同样的“扎经染色法”,即先扎染后织布。这与大理白族先织布后扎染分属两种工艺。和田农民的织绸机有一人多高,需要手脚并用。织机全是木质的,蚕丝的一端拴在一块大石头上,靠石头本身的重量将丝拉紧,工人则在另一端按设计好的图案将丝织成绸。吸聚东西方精华的艺术品站在一匹匹绚丽的艾绸前,我们总难免心生疑窦:是谁的妙手成就了如此美轮美奂的图案?其实,图案是通过扎染完成的。工匠根据图案需要,将经线用玉米皮扎起来,浸到矿物和植物的染料液中着色。扎经是非常细致而繁琐的工序,图案的形象、布局、配色都要在扎经艺人的妙手下才能体现出来。扎经完成后再分层染色、整经、织绸。染色过程中图案轮廓因染液的渗润,有自然形成的色晕,好像用干笔擦出的效果,参差错落,疏散而不杂乱,既增加了图案的层次感和色彩的过渡面,又形成了艾得莱斯绸纹样富有变化的特色。这就如同那些高明的画师,往往掌握着某些用色和运笔的绝技。在唐代以前,丝绸的纹样花色也同样主要借自于中原。
1995年10月,在和田民丰县,出土了一件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文字的织锦。卜辞为汉语自不必说,其总体风格和设计思想也显然受到秦汉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图案为星纹、云气纹及孔雀、仙鹤、辟邪、虎等瑞禽兽纹,华夏之风尚浓郁。值得一提的是,直到五代时,于阗国王李圣天(塞种人)仍然“衣冠如中国”,足见中原文化对于阗的影响之深远。至隋唐时代,新疆丝绸在纹样方面开始有了变化,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兼收并蓄的发端。新疆出土的大量隋唐时代的纺织品实物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些实物中以“联珠纹”“陵阳公样”“胡王锦”最具代表性。据研究,“联珠纹”主要来自波斯,“陵阳公样”主要来自中原,而“胡王锦”则是东西方文化结合的产物。一方面新疆的丝绸文化受到东西方的影响,另一方面,新疆丝绸也在影响着东西方。
公元10世纪,于阗国王曾带大批和田制作的“胡锦”“西锦”到中原进行商贸交易,在中原十分抢手。同时,在伊朗、土耳其及中亚国家的史书中也有过关于“艾得莱斯”的记载。艾绸上的“瓜果之乡”和田丝绸真正变成今日我们看到的艾得莱斯绸的模样,是在和田地区信奉伊斯兰教之后。公元16世纪整个新疆维吾尔民族全部信仰伊斯兰教,从此,伊斯兰教的影响深深渗透于维吾尔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之中。服饰文化自然折射出伊斯兰宗教的文化精神。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其他文化的遗痕。由于伊斯兰教禁忌偶像崇拜,所以禁忌在服饰、饰物和建筑物上描绘人物、动物。
故此,维吾尔族以各种花卉纹样,以植物的枝、叶、蔓、果实图案纹样,以现实生活中的壶、盆、瓶、炉、坛、琴等物的图案为装饰纹样,并以直线、曲线、弧线构成正方形、长方形、圆形、三角形、菱形、星形、新月形、锯齿形等各种各样的规则或不规则的几何图形,尽情装点着维族妇女的裙裤、坎肩,男子的袷袢、腰巾等。正是在这种宗教文化背景下,具有强烈民族特点的艾得莱斯绸问世了。
在图案中,最重要的实物象征莫过于“巴旦木”了。巴旦木纹具有明显的宗教含意,广泛应用于维吾尔人几乎一切装饰艺术中。巴旦木是“巴旦杏”的果核。这种杏树盛产于南疆,其果核形似新月,而新月正为伊斯兰之标志,故此,巴旦木图案成为维吾尔族极其看重的装饰图案。如巴旦木花帽的图案,就是由按前后顺序旋转排列的四个巴旦木纹样构成,线条丰富,花色庄重素雅。另外,艾得莱斯绸图案中瓜果、枝叶运用得较多,似乎流露了“瓜果之乡”和田人民的自豪之情。热瓦甫琴、独它尔琴的图案也很普遍,似又显示了歌舞之乡的特色。此外,对妇女喜爱的饰品,如梳子也多有表现。其中,图案直观易辨认者有之,强烈变形难以判别者亦有之。艾绸的色泽也与中原不同,鲜艳明丽,色彩反差大,与沙漠边缘单调的环境形成了强烈对比,隐隐透出此方百姓热情奔放、豪爽直率的性格。此锦只应天上有宋元时代,维吾尔族纺织工人创造了织金锦的新工艺,增加了织品的华丽,对我国各地都有影响。元朝政府对这一新工艺极为重视,把300余户织金锦工人调往甘肃安化一带,设局制作,为织金锦工艺的传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清朝末年,督办新疆军务的左宗棠,也看到了新疆发展桑蚕的重要性,为此采取扶持的政策,设立蚕桑局,曾招募浙江“湖州土民熟习蚕务者60名,并带桑秧、蚕种前来”。当时仅从长江下游运来的桑苗就有几十万棵。同时,还大量招收维吾尔族徒工,推广江南地区栽桑、育蚕、缫丝、织绸等先进技术,因而新疆蚕业曾有一定程度的振兴。上世纪50年代以后,和田的缫丝业逐步由机器代替了纺车。由于丝织技术的革新和金银线的引进,艾得莱斯绸更增添了许多新颖款式。不过,就像很多濒临失传的传统手工艺一样,由于保护和经营不够得力,艾得莱斯绸也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地方政府也在积极采取措施,例如,发展旅游,让游客参观制作过程、购买丝绸制品,扩大对外出口。当地的维族老乡们正重新捡拾起这门古老的绝活,让它再次传播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