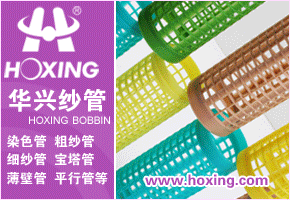马蒂斯的绘画与他的纺织收藏品
贝瑞·修瓦斯基/文
正如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在他的图腾学研究中声明,动物图像有助于拓展人类的思维。同样,亨利·马蒂斯(Henry Matisse)或许早就断定,纺织品也有助于启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与所有宜于展出的绘画一样,“布之梦——马蒂斯的绘画与他的纺织收藏品”,这场美轮美奂的展览竟被冠以一个相当笨拙的主题而成功举办。尽管博物馆馆长们总是试图在那些举世瞩目的大师们身上寻找新的视角,如莫奈、毕加索等,却很难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作品的新意。通常情况下,那些展出无非是让你重温一下昔日旧梦而已,或者是给你的旧梦添加上些许精神的脚注。而“布之梦——马蒂斯的绘画与他的纺织收藏品”,这场展览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成功地令一位家喻户晓的艺术家焕发出新的光彩。
敢于独持这种新锐观点,或许正是由于策划该展览的核心人物——希拉里·斯珀林(Hilary Spurling),其人并非艺术史家,而是一位艺术传记作家。希拉里·斯珀林是一位英国作家,她早期的著作在涉猎艺术之外,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两位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边缘角色的英国小说家的关注,这二人即康普顿-伯内特(Ivy Compton-Burnett)和保尔·斯科特(Paul Scott)。显然,斯珀林似乎并不是为这位现代艺术中心人物的法国人作传的最佳人选,但是,从她所作的马蒂斯传的第一卷中可以看出,(该书出版于1998年,第二卷现在刚刚出版),尽管作为一个批评性的图说者还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她却善于运用她锲而不舍的研究技能,去挖掘那些被虚构情节所湮没或忽略的重要史实。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发现阿尔弗雷德·巴尔(Alfred Barr)曾经称呼马蒂斯世纪之交的“黑暗时期”(这正是野兽派光芒四射之前的那一时段),不仅仅指19世纪90年代晚期是艺术家的蛰伏时期(此间,马蒂斯接受到印象主义和新印象主义的影响并臣服于用褐色来操控昏暗的调色板),也许有时候这正是一种思想的表达,因为其时他已患上了间歇性的精神疾病。事实上,这确是一个私人生活上的低迷时期,尽管无辜,却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他妻子的家庭受到那个时代最大的丑闻之一,亨伯(Humber)案件的牵连,该案件是一个数额庞大的金融诈骗。
亨伯事件对马蒂斯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许在他20世纪早期的艺术创作中还有所显现,但已经很难说有多大的持续性影响。我在伦敦皇家学院所见到的对“布之梦——马蒂斯的艺术与他的纺织收藏品”的评论,的确是卓尔不群的,几乎完全接近于画家艺术冲动的内核。马蒂斯的艺术植根于他的成长环境,他主要在皮卡地的小镇勒卡多长大,这是一个纺织工业占据日常生活的地区,因此,对这位未来之星来说,唾手可得的视觉感受(与自然不同)正是他艺术灵感的唯一源泉。正如斯珀林在书中所描写的那样,“那儿没有用于展出的画廊、博物馆或艺术收藏品,甚至连一座公共雕塑都没有,更别说是在这些烟囱遍布的镇上能看见一幅壁画。对于一个早已梦想挣脱樊笼的孩子来说,其萌生的视觉想象力,正是来自于遍及伯汉(Bohain)地区的织房和工厂生产出来的豪华的、炫目的、色彩缤纷的丝绸。”1同时,一些印着伯汉丝绸样品的精美书籍,也陈列在展览会上。(这些书籍为皇家杜马学院所掌管)当斯珀林论证自己对展览的独到见解时,就揭示了这些纺织物是如何点燃了一个男孩的想象力:绚烂而纯净的色彩,音乐般的节奏,生气盎然且琳琅满目,即便在今天,它们依然散发着一个世纪以前的清新,依然光彩照人,依然能点燃你的梦想。此次一共展出了80件马蒂斯的作品,其中大约40件为布料、地毯、帷幔、时装等类似的纺织品,这些藏品都是从他的“工作藏书室”精选而来,直到现在仍珍藏在艺术家的家里。无论从哪个层面,这些纺织品都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这也正是它成为画家艺术素材的关键所在。
在今天,传记研究已经很难处于艺术史的最前沿,但是也许它们应该复兴起来;可以说,斯珀林的研究只是沉浸在艺术家的创作生涯中作一种整体上的洞察。毋庸质疑,与现存的关于马蒂斯的文学作品更为熟悉的主题的拓展相比,说她在编目上所做的工作也同样是有价值的。杰克·弗莱姆(独自撰写了关于马蒂斯的传记:《马蒂斯和毕加索》,2003)从艺术家的作品中探究了他称之为“装饰性的结构”的发展;拉布傅斯(Rémi Labrusse)教授考虑到伊斯兰艺术对画家的影响;而多米尼克(Dominique Szymusiak)则分析了马蒂斯设计的为数不多的几组服饰中的一件,即马蒂斯为文斯(Vence)教堂设计的十字褡。然而,在他们之中,却无人真正地领会到纺织品在马蒂斯绘画中具有的本质的、内在的艺术内涵及重要性,就像斯珀林阐述的,“马蒂斯的祖辈,几代都做过纺织工。纺织品已经浸透在他的血液中,他的生命中已经不能没有纺织品。”2在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个展览仅仅是为该课题开了一个好头,而下一步的继续研究还有待时日。
与此同时,展览会还解决了一些基本工作,譬如:通过集中展示精挑细选出来的那些对马蒂斯的艺术创作有直接影响的纺织收藏品,便提供了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文本参照。展览中,我们发现一个颇具特色的例子,画家大胆地采用了一定长度的蓝色印染棉布——马蒂斯称之为《约依印花布》,(尽管大仲马指出它实际上比Jouyen Josas生产的洛可可式的印花布出的晚,直到1843年才生产。)在一种罗曼蒂克气氛与艺术历史性颉颃并进的喜剧电影习俗中,即主角应当符合“逗人喜爱的”角色。在1903年那黑暗的岁月里,画家驾驶着一辆马车,四处寻觅绘画的原材料。大仲马引用阿拉贡(Louis Aragon)的话说,“当标本被发现时,正如马蒂斯所描述的那样,总是一见钟情。在驾车旅行发现那一刻,这块布正悬挂在一家旧货店里。此后多年来,马蒂斯绘画一直采用那种材料。”
这块布料很快在作品《吉他手》中被运用,它悬挂在一片极不显眼的背景里。但是不久,它又在《彼埃尔·马蒂斯和彼得维尔》(1904)中充当一张桌布,它诡驈而出其不意地似乎要游离出画面平面之外。在该画中,它已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试探性的呈现方式,而是熠熠生辉地促使画中的一切其它事物都融入背景中。(除非在端庄怡人的静物花卉中,它仍然以衬托为主。)甚至在那些有名无实的肖像画中,以艺术家的爱子抓住一个宠爱的玩偶的题材为例,人物却被放逐于画面的视觉焦点之外;尽管艺术崇尚反叛自身——像野兽派那样,桌布促使它针对某种传统,但它似乎还没做好准备创造什么。那将在次年发生,正如《有蓝色桌布的静物》(1905-1906)中显示的那样,在这幅作品中,画面呈现出一种异常幽暗而朦胧的背景,到处被一些苍白的渐淡画和稀落的图式残留物覆盖,彷佛一挽薄纱帷幕以超越亘古的“黑色”手法被掀开。(事实上,这幅静物是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作品的上方,该作品孤零零地放置在那阴暗的地面上,显示出一种微弱的在场。)现在,《约依印花布》中图案与色彩所充盈的张力终于松弛下来,强烈感也几乎消褪了,但却为水果特有的橙色和黄色及其精彩绝伦的写意性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氛围。
然而,这仍然只不过是这块特殊布料传奇故事的序曲而已。1908年,它又恢复了《格丽塔·莫尔肖像》中的背景,但是相比较1903年作品不同的是:强烈的内在张力,粗犷地加强其装饰性,笔触环绕着坐者的头像形成一股漩涡,正如阿尔弗雷德·巴尔巧妙地指出,“以强烈的深色、亮色与淡蓝色图式为背景,为了生存而奋斗”4莫尔,对马蒂斯的艺术劳动非常熟悉,她的丈夫是柏林先锋派画家群中的一员,如同马蒂斯回忆道,她仍然“被我邀请她先生的举动和作品的效果所震惊不已。我看到他们完全被我的作品艺术魅力打败了,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灾难性的打击”5,不过,两天之后,这对夫妇还是愉快地安心于他们的绘画创作。在《有蓝色桌布的静物》(1909)中,作品自身又开始变得与背景协调起来,“现存的普通材料”,正如高文(Lawrence Gowing)偶尔提及的,谁若想表现,就必须一往无前地彻底开辟道路,披荆斩棘,为塞尚(Cézannean)式的小幅静物画提供养分和广阔的塑造空间。作为纯粹而可操纵的艺术表现介质,这布料意味
着垂直与平面的自然交错,在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的对立与冲突。
不过,与马蒂斯的巨作《红色的和谐》相比(1908),(由于彼得堡承受不起分开的绘画作品而错过了这次展示),《有蓝色桌布的静物》只能被称作为“一件小品”而已。在画中,桌布的蓝色被成高纯度的红色所替代,物象几乎以超越共性的方式进行变形,但是在以篮子和蔓藤花纹布料的主题中,融入一种坚固的现实性,与五年前《彼埃尔·马蒂斯和彼德维尔》中的桌布之逸笔草草相比,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它运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更加精妙的表现方式,似乎超越了物象与轮廓存在于空间的真实性。
因此,对于马蒂斯的艺术而言,这个关键的十年的星路历程就可能通过这件纺织品而被记录下来。马蒂斯仍然一如既往的对它倾心不已,在《石膏像和花束》中,他再次用到了它,虽然此处以纯直觉的背景元素呈现,很可能成为一种“现存的平凡媒介”,但它却具有某种可塑性变革的能力,通过它在《红色的和谐》中表现出来,同以往一样,除了情感与怀旧的缘故,它不再需要直接的引用。在《三色堇》(1918-1919)中,一个不太起眼的作品同样从《约依印花布》中抽离出来,作品的画面被密集的褶皱所分割,不管桌子角落的推力是如何的尖锐,它不惜采取强制的手段将其熨回原样,从而强有力地突显出自身的价值。
此时,马蒂斯已经进入到他创作生涯中的优雅时期。这正值战争期间,也许可以这样说,雷诺阿已取代了塞尚成为马蒂斯顶礼膜拜的先驱,他开始进一步去拓展想象力的纵深空间,同时也更加沉湎于感官上的享受。这次展览的一大成果就是澄清了马蒂斯艺术的连续性,不仅穿越了最激进的一战前岁月与优雅时期的断裂,也贯串了稍后时期与他回归到40年代的一个更加内敛的平面化时期。这个时候,正如克莱蒙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所称,“说起众多艺术家,马蒂斯已经重返至一种富丽堂皇的艺术风格,同时又有一种令人震撼的、意味隽永的朴素性,这一切皆使他与众不同。”8观看优美的图片,由于图案平面化的维系,从而塑造出一个更加开放而妖娆的女性身体形象,与图式和色彩的复杂构成相比,你很难由衷地出自感官上的满足来欣赏它们——尽管它们理所当然要保持原样。于马蒂斯而言,享乐主义的幻想(尽管它伪装成一种相当保守的自然主义)较之目标的设定更加是个诱惑。二十年代期间,马蒂斯对纺织品与时装的收藏已真正初具规模,就是这次展览的首次面世。可以想象,这些年来,作为一个具有感知力的流动剧场的经营者,他从一个旅馆搬到另一个旅馆,就像任何一个游牧人一样,他不得不将他的装备打理好,为下一站整装待发。
那些图案与平涂的色彩是如何造就了马蒂斯的审美情趣,以及纺织品又如何与他的创作经验溶合,这一点已不难理解。从双重意义上来讲,他在绘画中注入的纺织品和时装其实就是一种“模型”,就像马蒂斯描绘与它们在一起的人们,不仅作为个人及自发存在的主题,而且刻画手法的例子也是如此。甚至在很多作品中,他们扮演的都是后者的角色,这样,他的纺织收藏品就无需直接露面了。例如,在马蒂斯晚年,正如斯柏林指出的,非洲与波利尼西亚的纺织品,以大胆的手法加以图案装饰,呈现出不规则的方式,由于是手工编织,令马蒂斯在如何重铸强有力的平涂法上获益匪浅。在二、三十年代的优雅时期,这种技法曾一度被他放弃,尽管他晚期作品图式中光彩夺目的色调已远远去掉了这些纺织品的土质颜色。在马蒂斯晚年的剪纸图样中,已不再存在纺织品作为绘画主题的问题,但他仍然以纺织品为样本来思考绘画。
总体而言,作为绘画的范例,马蒂斯所借鉴的纺织品除了来自欧洲,还包括来自伊斯兰的、波利尼西亚和非洲的纺织品的运用,这反映了他对文艺复兴传承下来的主流传统的怀疑态度。对于日本印刷品和拜占庭式雕像的迷恋,则又反映了一种类似的冲动体现在他重复依赖性的工作中,同时也体现在他的文学与艺术创作中。意识到这点,同样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并接受马蒂斯在《画家笔记》中所作的极易产生歧义的名句,这也他对自己创作经验最广为人知的总结:“我的梦想是一种均衡的、纯粹的、安宁的艺术,其中没有令人烦恼或令人沮丧的题材,它是一种智者的艺术,对于商人和送信员也一样,譬如抚慰、安宁对大脑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为疲倦者提供一张放松的扶椅。”
显然,由于这段文字一再提到商人,从而提升了马蒂斯作为一个资产阶级轻松情调与乐趣的进贡者形象。但商人被援引,不仅是作为其艺术品最理想的归宿,而且他们也确实至少可以被看作其受众者之一,这与送信人则形成鲜明的对比。(比较1846年波德莱尔沙龙“对资产阶级来说”的开头部分,他敦促那些在艺术上错误地忽略美的唯物存在论者,需要一杯清醇温馨的饮料来恢复头脑和肠胃对理想美的自然平衡状态。10)换言之,马蒂斯的声明对精英分子来说是一个辩词,包含着艺术的所有特征,它的能量甚至熏陶了那些对艺术缺乏自觉理解能力的人们。后来,马蒂斯又放出新的高论,这被人们视为对前面那段话的矫正与修订,他严厉指责“那些被错误地定位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们”,在他们的作品中,马蒂斯发现“一流的纺织品是为富人而创造……其物质价值远远超过了精神价值”。在这里,文艺复兴艺术被视为艺术家唯物主义倾向的缩影,画家们为富人创作代表财富的作品。然而,事实上马蒂斯也常常用“绝妙的纺织品”来自我定位,在作品单纯的物质价值之外,他往往会追求并诉诸它们一些别样的东西。的确,我们应当认真地采纳斯柏林的直觉,是他发现了马蒂斯绘画存在于纺织品之中的第一秘密——“在价格之外,一切为我自由利用”,正是这些纺织品,最初打开了那个伯汉男孩的视野,尽管他早期耳濡目染的华丽的丝绸委实是奢侈的商品,在价格上与他自己后来收藏的也无法同日而语,这无疑是马蒂斯的所思所想。就在他撒手人寰的前几年,他宣称,艺术家应当“将生活看作是孩提时代的玩耍”13。马蒂斯强调的纺织品的视觉普遍性与另一位伟大的色彩画家丹·费拉文(Dan Flavin)并无差异,这种视觉普遍性,他后来称之为“人所皆知的视觉的中性快感”,尽管它与费拉文具有的“心理漠然”大相径庭。
- 羊毛纤维服装保养 (11-09 11:01)
- 值得收藏的五款秋季鞋(图) (08-11 10:07)
- 当代服装被收藏 东北虎华服入驻首都博博物馆 (05-17 10:53)
- 普拉达珍藏版商品5月出售 (04-28 09:10)
- 澳大利亚原住民丝绸画收藏精品展在沪开幕 (11-14 1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