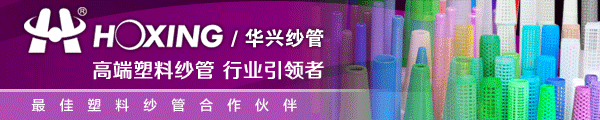种棉花的苗家人
四年前的“五一”,我随同旅游业资深人士周先生,去到了深山里的苗寨——台江县南宫乡白帮村白帮寨。从乡里到白帮的乡村公路沿着乌密河蜿蜒而行,清澈的河水尽收了两岸无边无际的翠绿。不通班车,路上深深的车辙间已是芳草萋萋。20公里的路程,乡里租用的货车颠簸了1小时50分。
车已无路可行,白帮还在大山里。后生们吹着“母芦笙”、“中爸芦笙”和“崽崽芦笙”,簇拥着我们徒步上山。羊肠小道上不时可见芭茅叶打的草标,标示着主人的种种禁忌。远处突然响起了带颤音的飞歌,白帮的姑娘们兴奋起来。原来,是远处来的后生远远看见这么一群姑娘,歌声就飞过来了。姑娘们先有些害羞,在我们的怂恿下,终于也以飞歌作答,饱含了真情的天籁之音在傍晚的深山里久久回荡。据说,这种颤音是模仿蝉鸣,在发声学上,有没有将这种流派纳入视野?
白帮寨只有105户,全是苗族。祖先从哪儿来?61岁的邰玉清说汉语十分流畅:“老祖先原来在江西,那时我们姓姜;后来到了南虎城,我们改姓赵;老祖宗养九个崽,帮人抬轿子进山来,来到这里,大家都改姓‘邰’,邰姓从我往上推,只能推出四代人的名字。”
白帮家家户户至今还种棉花。
路边有两棵巨大的枫树,那是他们的图腾树、神树,春节和“二月二”祭树的时候,除了常规的祭品之外,还得敬上棉花。尊贵的“母芦笙”上的装饰,是雪白的棉花。请鬼师来做巫事,没钱可以不给钱,给点棉花表示心意就行。而白帮的棉花歌,更是人人会唱。在邰家,两位后生倒了三碗酒搁在面前,然后用高亢嘹亮的颤音唱起了《棉花歌》。棉花歌唱出了种棉的起源,以及从挖土、撒种、薅棉、掐花、纺线、织布、漂染的种、染、织全过程。
“祖先逃进深山老林,只有用树皮遮身。嫂子与哥哥一同上坡,开一块荒地种棉花。我挖坑,你下种,棉花苗木长势好,杆杆就像锄头把……棉花收了,大家过节。男男女女穿盛装,姑娘裙子穿五层。后生吹芦笙,女人煮饭来。男人喊客到家里,棉歌人人唱,米酒人人醉,苗家年年来相会。”
后生们唱了棉花歌,又用藏青色的布条来打包头,布条是2—4根,一共五六米长。先量好头围的大小,就在膝盖上熟练地编花,六七分钟就能编好一个精致、厚实的包头。
女人边听边唱《棉花歌》,手脚都不闲。她们坐在特别高的纺纱凳上,用一种脚踏的纺车纺线。坐姿显得亭亭玉立,双手抡线的动作,犹如优雅的舞蹈。
贵州曾经大力提倡种棉。20世纪60年代,省委机关干部们带头在南明公园种起了棉花。可是,棉株结桃却绽不开花,干部们的收获是一人分了一两丈布票。历史总是会捉弄人,进入21世纪,在贵州最边远的农村,要找到一处依然种棉花的地方,也非常不容易了。
一件农事,一样种植,会因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种棉花在白帮不单单是一件农事,它已经成为一种信仰,一种文化。这里的重大事项都离不开棉花。所以,它就不大可能像战天斗地的机关干部们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说种就种,说停就停。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白帮苗人的种棉习俗前景莫测,但关于棉花的文化却会永远留存在白帮苗人的记忆之中。行政手段是一时的,而要保留一种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最根本的,是要保护好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