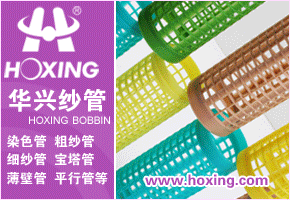中国制造:涨价潮中的女买手
■中国制造提价
汹涌而来的涨价潮,改写了国际采购者的日常生活。作为中国制造输往全球的第一个环节,买手们最先感受到了潮水袭来的苦楚
“如果今年夏天还找不到男朋友,我就飞到欧洲找大老板理论去!”
7月13日晚11点,在上海衡山路的一间酒吧里,邹琳(化名)向她的姐妹抱怨。30岁的年龄,在上海,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找个男朋友总不算奢侈。可是,她没时间找,准确地说,她没有心情找。
邹琳服务于欧洲某大型体育用品专营企业。这是一家跨国公司,集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在全球25个国家有近3万名员工,去年销售额是45亿欧元,其中三分之一的产品由中国制造。邹琳是上海分公司的一名买手(负责采购的人,业内俗称),负责登山鞋的采购。
去年10月份以来,她的心情就像中国的股市,始终没有真正露过笑脸。她不断地周旋在供应商和商场之间,有时像夹缝中的小草,有时如热锅上的蚂蚁──这一切皆由“中国制造”的变脸所赐。
去年,邹琳是一周去泡两次吧,现在,她两周难泡一次吧。她不停地跟男人见面,但就是产生不了爱情荷尔蒙──这些男人几乎清一色是供应商,邹琳的工作,就是跟他们谈订单、讲价格、聊管理。
她脑子里装满了“谈判”二字。每天早上起来就是看原材料行情、政策和汇率变动,从公司系统后台看一下全球各商场的库存情况,然后就是琢磨着当天跟供应商的谈判,要注意什么什么细节,随什么机应什么变。
“如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嗖嗖地升,原材料价格突突地往上涨,我们只好把以前的大订单拆分、长周期缩短,来避免那帮供应商一下子给我们提价太多。”邹琳说。
一件事掰成几件事做,工作量和繁重程度当然变大了。邹琳所在公司有一个理念,不一定找要价最低的,而要找最适合自己的。符合这一理念的供应商一般是中等规模、在行业内排在第三或第四位的鞋企,这类江浙企业如今在谈判桌上正逐渐“硬气”起来,少了过去竞相压价抢单的激情,多了几份据理力争的理性。
“你不知道他们现在多牛气!利润低于10%宁愿不接单。”邹琳很不高兴。
这或许正是国际大品牌的“不幸”──如果要寻找新欢,替代“蛮横提价”的旧伙伴,时间一般需要3个月至半年时间,如果由此导致国外的商场断了货,问题可就严重了!
和小买家不一样,声名在外的国际品牌,“羽毛”太重要,不能不珍惜,在选择供应商时,他们没法绕过一系列程序——全套的调研,然后还得请第三方机构对目标对象进行社会责任(劳工保护、环保)等方面的认证。
这都需要时间。如果邹琳找到中意的供应商,经上海的上司确认后,欧洲总部还会专门派人过来查验,确保没有瑕疵。
公司的官方表述是,“寻求与供应商达成一种长期的伙伴关系”。不过,从这一点也能嗅出跨国公司对买手权力的制约。
邹琳是“打飞的一族”。她频繁在上海、温州、宁波、南京等地之间飞来飞去,目的就是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和客户“交心”上。
“如果真能交上心就好了!”邹琳苦恼不已。国内的供应商越来越精于算计,谈判技巧也越来越高超,他们不得不接受20%左右的提价,“我们甚至得频繁用到记者们用的录音笔,把谈判内容录下来,回去反复研究。”
如果能交心,说不定还可能找到个帅气的供应商男友?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连谈判地点也有学问──如果是谈价格,我们会选在供应商的办公室见面;如果是谈新产品开发,我们会去到供应商的工厂。我们绝不会在酒吧、桑拿等场所谈事情。”说到“桑拿”二字时,邹琳的语调明显提高了点。
她话有所指。去年以前,邹琳在上海一家民企做采购,那时的供应商为了争到订单,用尽浑身解数,令她印象深刻的一次,是一位供应商请她的男上司到夜总会“小聚”,找陪唱小姐,一人找仨,可谓“大手笔”。
邹琳受不了这种江湖习气,于是抽身而出,在去年初来了这家欧洲企业。不过,标准化的采购程式,让她有了另一种郁闷──她必须找到“技术性”的突破口,也就是说,她必须用各种办法化解涨价压力。
他们找到的“技术性”手段包括:更换产品中比较昂贵的原料,比如将金属鞋扣换成塑料的;在换汇上,和银行达成协议,一段时间的走货,根据升值预期,折成一个固定汇率,“比如今天的出口汇率是6.83元,预计3个月后会升值4%到6.56元,那么可以约定这3个月出口时使用一个折中价,比如6.7元。如果集中在第3个月结算,就会划算得多。”
还有“技术含量最高”的一招——帮助供应商改善内部管理。刚开始邹琳听上司讲到这一招时,觉得不可思议,不过她很快发现,如果他们和供应商一起在社会责任、物流、人力资源和质量管理等方面发力,最终确实会双赢,后者效率提升了,可以部分消解成本上升的幅度,价格也就有可谈的余地了。
注重长期合作关系的一个弊端是,可能会“宠坏”供应商,他们底气足了,觉得加价的筹码重了,可能会在备货过程中突然变卦,单方面要求加价。另一方面,一些供应商因为各种原因最终没有拿到订单,于是开始利用传媒宣传自己的“品牌意识”,斥责采购商的“不合理定价”。
“碰到这种情形,很尴尬,很无奈。”邹琳说。
她感到庆幸,所在的这家公司通过集约化的运作节约了不少成本。公司在中国有十多家分公司,之间虽然有竞争,但根据产品的地域优势划地为界,各分公司间采购的分工也就明晰了。
另一方面,尽管谈价格和下订单,以及供应链管理之间紧密关联,但由不同部门完成,如此一来,权力分散并互相制衡,避免了有人从中吃回扣变相提高成本。
然而,提到自己的薪水时,爽朗健谈的邹琳突然沉默,始终不愿开口。最后还是她的一个死党发话了:“这丫头年初工资涨了30%,现在也不过一个月不到一万。”
死党接着说,涨的这30%,还是邹琳反复申请和要求才勉强争取到的,在遭遇“中国制造”的涨价潮后,公司对这些精明勤勉的中国买手也开始吝啬起来,对原先的加薪承诺含糊其辞。
提成呢?“哎!”邹琳终于憋不住了,“订单等于是大家一起在做,所以严格来讲不存在提成一说。我们只是每个月发点奖金,当月工资10%以内。基本是等于一年发13个月工资啦。听起来像一个公务员,但我们的地位又差人家公务员一大截。”
在“中国制造”的链条上,似乎每一方都在说自己是“弱势群体”或“准弱势群体”。邹琳最后说,她大不了不干这一行,日子总得过,男朋友总得找,婚总得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