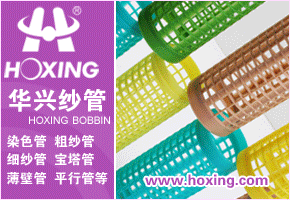雅克·卡普兰,一代“皮草艺术家”辞世
无论是在艺术界还是时尚界,1963年发生过的一次艺术家与皮草商的会见让双方都非常难忘。简约派画家弗朗特·丝特拉(Frank Stella)头一回以皮草大衣为“纸张”,绘上黑色和黄色的条纹;欧普艺术的领军人物理查德·安努斯科维奇(Richard Anuszkiewicz)则设计出一种粗大的白色几何圆点,画在一件小牛皮外套上。他们身后,这次活动的策划者,带着一个幕后指挥该有的那种微笑,注视着这一切。
他就是雅克·卡普兰(Jacques Kaplan),前半生勾勒出一个荒诞主义皮草商的形象,用新颖多变的皮草设计在时尚界掀起波澜,之后又默默沉醉于艺术世界,得来一个“一代皮草艺术家”的名号。7月24日,雅克因食道癌死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家中,享年83岁。
环保热潮席卷世界的现今,“皮草艺术家”辞世的消息显得有些“轻微”。但艺术界与时尚界忘不了他,正是他给皮草注入新的活力,实现了艺术与时尚相结合的初次尝试。用他儿子帕斯卡(Pascal)的话来说,“曾经的皮草市场,是由人工水貂皮服装铺设的一片宁静。”但卡普兰却做出种种“调皮”的事情,令其保守的父亲、第五大道和五十七大道上两家家族皮草商店的拥有者乔治惊骇不已。
越野性越卖得快
“他总能想出主意让生意变得有趣、刺激,很容易就能吸引一个新的客户”,帕斯卡说起父亲卡普兰,“他喜欢创造一种他爱的‘噪音’”。
卡普兰爱把自己的姓发音念得拖长一些,“Ka-Plahn”,这是出于法语的习惯。他1924年出生于巴黎,被从事皮草生意的大家庭环绕。这项生意从他外公自俄国移民至法国时就开始了,再由他的父亲以传统的方式接管——万事求平稳,有什么做什么,最痛恨冒险。
1942年,父亲把家族迁移到纽约,在第五大道重建了皮草生意,而卡普兰却离开了,他先进军校,再参战,还因勇敢生猛的表现被授予荣誉勋章。人们认为他奔放的性格成因和这一段野性的年轻时代不无关系。
卡普兰在巴黎大学修习过哲学,本想去教书,但是当他与法国著名银器商家族的克劳德(Claude Puiforcat)结婚后,即被父亲召回纽约,进入家族生意的管理。他首先关注到了年轻消费者的需要。“它们越野性,就越卖得快。”卡普兰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地说。
为了讨年轻顾客的欢心,他用一些不算很稀有也不昂贵的材质,设计出价格相对低一些的皮草,比如狼皮和野兔皮。谁料想,这反而开创了一个新的皮草种类——当时的有钱人轻蔑地称之为“下等杂色毛皮”,不过却成为现在流行的“fun fur”的始祖。环保盛行的21世纪,人造皮草照样时尚,也是fun fur的一种。
卡普兰还引入了一些奇异的皮草,比如蟒蛇皮、美洲虎皮、野生羚羊和印度大额牛皮,然后用创新的方法使用它们,令当时的时尚界大吃一惊。
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一天,卡普兰在自家店铺附近散步,偶然走进了一家艺术画廊。他被一幅画迷住了,并用一张皮草与之交换。这一次火花四射的碰撞使他沉醉于艺术,开始进入纽约艺术界,在那儿,他就像“在家里一样如鱼得水”。
他的高明之处,除了大胆,还有对皮草原料不遗余力、不乏创意的利用。他认为家具设计是一种艺术,因而开始创造皮草家具。他雇用知名艺术家来发扬自己大胆的创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席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的妻子贝碧·佩利(Babe Paley),是皮草家具最著名的拥趸,她甚至在浴室的地板上铺着一块从卡普兰那儿买来的地毯——用印度羔羊皮制成。卡普兰在宽敞的店铺前院摆放着最时新的皮草出售,便于开着车的客人不用下车就进来溜达一圈——这纵容了那些顾客养成用皮草来装饰车座椅的习惯,他们甚至连家里的储藏室门也要做一圈皮草装饰线!
从那时候起,皮草和艺术的结合就风起云涌了。当时的舆论对此展开猛烈的攻击,认为这是亵渎了艺术。特立独行的卡普兰沉浸在自己的爱好中,他给艺术家完全的自由,去发挥想象力。那个时期,卡普兰被描绘成“一个善于社交的禁酒主义者”。他不爱喝酒,却经常在纽约东部的家里举行奢华的晚会,招待他喜欢的那些波希米亚式的朋友。通常,疯狂的夜晚结束后,还会送他们去Westbury酒店享受一场舒服的睡眠。“我在第五大道,过上了一种西部牛仔般的疯狂生活。”他曾经回忆道。
让自己快乐,让喜欢的人快乐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卡普兰终于不再对皮草市场感兴趣,1969年,他把皮草公司卖给了Kenton Corporation公司,自己则依靠在艺术界的广泛资源做起了经纪人,安排收藏家、艺术家、画廊之间的联系和交易。80年代早期,他在肯特镇买了一幢房子,立志要把它打造成康涅狄格州的艺术中心。四年后,他真的在火车站边的一节货车车厢里,创造了一个“巴黎纽约肯特艺廊”,他把自己最爱的艺术家聚在一起作展览,也展示自己收藏的艺术品。他还总是劝说别人也开艺廊,当对方真的这么做时,他果不食言,大力扶持。
晚年的卡普兰是平静而丰厚的,妻子、儿子和女儿陪伴着他——前妻克劳德和他的关系也不错。他还有两个姐妹、四个孙子、三个曾孙。
“我人生的目标其实就是尽可能快乐,再让我喜欢的人尽可能快乐,”他曾经这样说过,“这其实是我们的社会唯一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