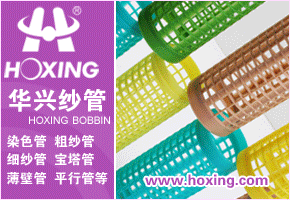一个家庭的60年纺织情缘
生意社9月3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我们这个家庭与纺织工业的情缘也延续了60年。从一个普通纺织工人家庭的变化,可以看到祖国的进步,看到中国纺织工业的巨大变迁。
据我母亲回忆,1949年前后,家里是靠做袜子手工缝口养家糊口的。解放后,母亲到被服厂当了一名纺织工人。1952年,听说纱厂招人,她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当时进纱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仅要求严,而且要考试。母亲没上过几天学,硬是在家补习文化,通过了考试,进了当时的震寰纱厂(后改名为武汉市第五棉纺织厂)当了一名值车工。
武汉有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当时我家住在汉口,而震寰纱厂在武昌,每天上班需坐船过长江,从家到船码头还要走半个小时。家里没有闹钟,遇到上早班,全凭外公听屋外清洁工、小贩的车轮声和脚步声掌握时间。有时,起床走到船码头,方知早了一个多小时。
母亲是坚强的,也是敬业的,在震寰纱厂工作几十年,从未迟到、早退,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动乱的年代里,她仍然如此,而且经常加班加点。在她眼里,纺织工人工资高、地位高,她为做一名纺织工人而感到自豪。
1966年,母亲厂里在武昌建了新的职工宿舍,我们家三代七口,分到了23平方米的新房子,虽然3家共用厨房和卫生间,但比原来一家人挤在9平方米的小房子算是一个解放。有了工厂附近的房子,有了闹钟,母亲再不用外公凭感觉喊她起来上班了,也不用担心雨雪和长江上的风浪了。母亲工作的干劲更大了,经常立功受奖,在儿女们眼里,母亲是勤劳、能干的。
母亲除了自己努力生产外,还希望自己的子女也成为纺织工人。1975年,我作为知识青年下乡已3年半了。当时我是湖北省五三农场的劳模和标兵,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此时,母亲坚决让我回武汉“顶职”做一名纺织工人。农场领导说:“彭继汉在我们这里已经是国家干部了,不能回去‘顶职’。”但在母亲的坚持下,工厂出面与湖北省农垦局协商,终于把我从农场调到了武汉市第五棉纺织厂。
进厂后,母亲希望我当一名纺织工人,不要当干部。她认为:工人地位高,再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学门技术,将来生存就不怕了。但当工厂党委坚持要将我这个年轻党员放在干部岗位上时,她也就不坚持了。1978年,我被组织派到武汉市委党校学习了一年,回厂后,被正式安排在党委宣传科工作。从科员、科长到市纺织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直至现在的党委政治工作部部长,一干就是30年。虽然没有满足母亲让我当纺织工人的愿望,但我始终没有离开纺织行业,通过手中的笔和相机,我记录了30年来武汉纺织工业的巨大变化,讴歌纺织工人的感人事迹,与纺织工人同喜同乐。
现在的武汉纺织行业,虽然一批老纺织企业破产重组了,但像武汉江南集团、裕大华公司这样的企业发展了,一批民营纺织服装企业壮大了。如今的纺织厂里,母亲当年用的筒子车早已被淘汰,新型的全自动络筒机大大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纺织企业从市中心搬到郊区后,新厂房更明亮了、噪音降低了、灰尘减少了。像江南集团这样10万锭以上的大厂,过去需要7000名工人才能保证生产正常运行,而现在,3000名职工已绰绰有余。
再看看我们的家,现在,4个兄弟姐妹均走出了那23平方米的小“窝儿”,各自有了两室一厅或三室一厅的住房。根据母亲的意愿,我娶了纺织女工为妻。特别是从武汉科技大学毕业的儿子,毕业论文也是以纺织贸易为题目,还得了优秀奖。回想过去的60年,我们家真是与纺织有着深厚的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