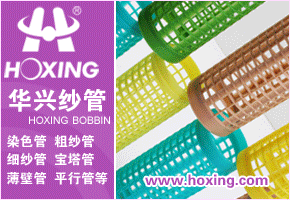记者卧底东莞打工:每天离厂的人比进厂的人更多
生意社7月27日讯 ◎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
◎在赶工方面,所有厂都“一般黑”,工人订单少时愁死,怕被炒鱿鱼,订单多时累死,每天10多个小时,绷着的弦一刻也不能松。
◎不要问这些兄弟打工累不累,苦不苦。每年8月底,你到汽车站去看看,家长送小孩回家,小孩在车上哭,父母在地下哭,看到这一切你就都会明白
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生在农村,却五谷不分;受过一定教育,却不足以在城市立足;非城镇户口,却每天在城里逛街、追星、用苹果手机———尽管是山寨的;他们的当务之急,是拼命赚钱,终极目标却不再如父辈一般,回老家盖新房……
他们十七八岁就进了城,在城市拼命追寻,企求在异乡开辟一片新天地,可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鲜有结果。他们咬定青山不放松,还在向前走……他们,用个专有名词来称呼———新生代农民工。
7月中旬,南方日报记者以普通农民工的身份,在广东东莞求职应聘,顺利进入一家制衣厂和一家玩具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周,管窥他们的生存、困惑和迷茫的未来。
第一天:找工近九成新民工不会农活
东莞,中国农民工集聚地之一,这里有数不胜数的大小工厂,每年众多农民工从全国各地涌向这个弹丸之地。2011年7月11日,我从广州出发,前往东莞揾工。
“大量招男女普工”,东莞街头满大街的标语,对于刚来求职的年轻人是一剂强有力的兴奋剂。我应聘的第一家厂是虎门镇某知名电子厂。上午8点到达厂区时,排队求职的队伍已绕了一圈。和其他求职者聊天得知,能到这样大厂来求职的人,多是受老乡指点,或者在别的小厂做不下去了,初次到东莞的人,“看到什么厂进什么厂,很少会挑这样的大厂”。
求职成功的人告诉我,即使是和老乡或者朋友一起找工,也不要站在一起。“如果超过三个老乡一起见工,百分之百被拒”,他说,现在的年轻人爱闹事,爱拉帮结派,工厂会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两个熟人进同一个厂,一般都会安排在不同的宿舍,不同的生产线,减少彼此之间的交流。等到9点半,当天招聘满额,我和排在前面的数十人被告知第二天再来。一位应聘成功的小伙子告诉我,他凌晨3点就过来排队,“不要急,别看他招得多,每天离开的更多”。
接着,我来到长安镇一家颇有名气的人才市场,工作人员指着招工广告上“世界500强”大声问,“这个知道怎么回事吧,世界500强,不得了的!”一声吆喝,众多求职者凑了过来,这位工作人员承诺,交220元,包进名厂,包分配到“最轻松的岗位”。不过他再三强调的是,反悔了,不退钱。
每天离开工厂的人,比进厂的人更多。这并不夸张。我打工时住在下铺,上铺的主人一星期换了两位。进厂做工的枯燥和压抑,让不少原来只想玩玩的年轻人后悔不已。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颇为相似。
第二天:进厂不加班者按旷工处理
我在东莞打工生涯的第一份工在制衣厂。厂区墙壁上贴着巨幅招工广告,我走进去碰运气,才发现由于急缺工人,这个厂的招聘变成了走形式。手臂没纹身、10个手指没断指、说话利索,被检查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后,我出乎意料地轻松入职。每月工资底薪920元+打分提成。早晨6:45起床洗脸刷牙,吃过早餐到工厂刚好7点半,拿着工作证刷卡进车间。在等待组长分配任务时,和一位湖南大姐聊天,她自言自语说,“这么年轻做拉布,看你能做几天”。
组长是位30多岁的四川人,他把我带到一个整理原料的裁床前,要求我和两个刚入厂的十几岁的小孩一起,按照单子的要求,将不同颜色的布料分类捆绑。从8点到11点半,一直就是按着单据整理布料,一个上午下来,脚有些酸,但起码还没有那位大姐说的那么恐怖,我有点幸庆找了份不错的工作。
食堂吃饭是免费的。进食堂前,心里做好了充分准备,但望着食堂师傅饭盆里的清水煮冬瓜、豆芽和茄子,心里还是很失落。吃饭时,我不时看着边上的工友,不知道他们怎么吃得下去。下午1点半开工,组长领着我将一个机器拖到车间,下午的工作是解开车间未开封的布匹,扛上机器,通过机器打开布匹,再按颜色分类整理堆放,以备上裁床裁剪。
一捆布三十来斤,我肩膀没力,只能用手抱着放到机器上,抱到第七捆时,早已经汗流浃背。十几捆布下来,已经累到不想讲话。休息时,一位暑假工模样的工友,给大家讲起了大学生活。他的高谈阔论有许多卖弄成分。听到他说下学期奖学金有5000元时,一位工友的嘴巴明显张大了许多“不用干活,也有5000元?”
“说这么多也没用,再回去高考一次照样考不上,照样要出来打工”。另一位工友回应。短暂休息后,新的任务又来了。一捆一捆的布要一寸一寸拉平,需要两个人一人捏着布的一角,拼命地往前跑,用跑步的速度带动布捆转动。手不能捏得太紧,也不能太松,但跑步速度却要快。“你就想象后面有条狗在追”,组长说。跑完以后需要原路返回,用手轻轻将布抚平。
接下来的5个小时,我就这样一趟一趟地跑。车间的吊扇仿佛根本不存在,身上的汗就像雨水一样往下淌。由于是生手,我屡屡出错。开始组长还在一旁盯着,但后来见我出错太多,他已无力顾及,临走时留下一句话,“工资主要靠提成,提成根据工作表现打分,你这样做一天,还得赔钱”。一旦出错,整个小组都要返工,工友们的工钱就会受影响。一位工友最后还是说话了,“给你两天时间,如果还做不好,就换个组吧”。
按照工厂规定,晚上要从7点半加班到10点或11点,加班费5元/小时,不加班者按旷工处理。下午下班后,饭都没吃,我就直接回了宿舍睡觉。第一个工作日终究没能坚持下来,我逃掉了第一个加班。
第三天:丢钱没丢过东西打工不完整
工厂宿舍房间24小时不上锁。入住宿舍前,管理人员再三强调,财物自己看好,“即使是老乡也不能信任,知人知面不知心”,宿舍提供给每人一个铁柜,自己买锁,自己看管,“反正我都提醒你们了,再丢了东西与工厂无关。”同宿舍的一位工友,平时身上的现金不会超过50元,用完了去ATM排队取钱。有时凌晨一两点,不少ATM机前的队伍还能排到马路上。银行卡和身份证是最重要的两件物品,这位工友装在内裤前面的小口袋里,虽然好几次洗衣服忘了拿出来,但他仍坚持用这种方式。
7月13日傍晚下班后,我准备去厂外买盒饭。一天的劳累,人早已筋疲力尽,精神开始恍惚。要了一份最贵的快餐,一摸口袋:空的!我顿时呼吸急促,血一下子冲到脑袋,身份证、信用卡和1000多元现金全在钱包里。
扫了一遍快餐店,确认没掉在地上后,我迅速原路返回,但意料之中的一无所获。扩大范围找了一圈后仍没有收获。在工厂里丢了东西都与工厂无关,出了厂门,他们更不会理睬。我只好拨打110报警,接电话的人说,这样的事情,要向最近的派出所报案。又拨打派出所电话,对方称身份证丢了不需要挂失。我一直坚持要报案,他才答应派人过来了解情况。
两位身着“治保”服装的人见到我后,笑嘻嘻地指着不远处一座桥问,“是在桥这边丢的,还是在桥那边丢的?”“在桥的那边,我打110后他要我联系你们派出所。
“在桥的那边,就不是我们的管辖范围,你应该在那边再打报警电话”,说完,两个人离开,剩下目瞪口呆的我。此时,快到晚班时间,我只好返回工厂上班。工友告诉我,“没有丢过东西的打工,是不完整的打工,丢了东西很少报警,反正没有用”。
第四天:换厂一个月工钱经不起罚款
制衣厂工作两天下来,我有点吃不消,而对于我不愿意加班,主管也不满意。双方很快“达成一致”,我辞工走人,没有一分钱的工资。临走前,主管说,“比你时间短的人多得是,有的年轻人只做了半天”。找第二份工作,我瞄准了某大型玩具厂,标准的流水线作业、厂内清一色的“85后”。这家工厂很受欢迎,要进厂得早起早准备。当天清晨5点多,我就到了厂区外,没想到已经有近百人排队。据说前几天,陆续有100多人辞工,所以当天招人数目不少,我再次顺利入职。每月工资底薪1100元+计件提成。
玩具厂的工作相对简单轻松,但几天做下来,心理压力却丝毫没有减轻。我被分在玩具娃娃生产线上的最后一道工序———将前面11道工序组装好的产品,按标准装入包装盒,哪里贴胶布、哪里折叠,都有明确而细致的规定,稍有不符,就要重新回炉重做。我和另外两名操作同样工序的人,分到了编号各异的包装盒,一旦出现差错,组长就能根据编号找到责任人。
除了组长,在生产线上来回“巡逻”的还有技术工,他们与组长平级,同时检查监督若干个组的生产质量,要求不达标的产品返工。工人对这些技术工又爱又恨,刚进厂时,自己的手艺来自于技术工传授,但短暂学习后,这些技术工从老师变成了监工。
组长、技术工轮番轰炸,给工人带来的压力是摧残式的。做工时,我想到了富士康一位坠楼幸存女孩对我说过的话。2010年,我在深圳采访富士康工人连续跳楼事件时,这个可怜又幸运的17岁女孩说,“从上到下,不断向我们强调,一切向效率服务,一切向速度看齐”。她告诉我,同一条生长线上,有老员工,也有像她一样刚进厂新员工。但对产量的要求却不分新老,看着老员工轻车熟路,“我越做越急,越急越错”。只要速度慢下来,主管领导就会拼命地催,有时还骂脏话。
换过不少厂的工友说,在赶工方面,所有厂都“一般黑”,工人订单少时愁死,怕被炒鱿鱼,订单多时累死,每天10多个小时,绷着的弦一刻也不能松。虽然是坐着,但货物源源不断从生产线上游往下走,我又是新手,时刻要保持高度紧张,很快就腰酸背痛。我换了个舒服的姿势,蜷缩靠在椅子上,手中的活并没有停下。但不到一分钟,管理员指着我大声说,“坐好,坐正!”看见我是新人,他又补充了一句,“没有好的状态,怎么能出效率,没有效率,一个月工钱经不起你罚钱”。
加工制造企业的盈利模式,对效率有着歇斯底里般疯狂的追求,工人做熟了某一道工序,为了提高效率,他就会固定在这道工序上直到他离开工厂。被问到“这样的娃娃要卖多少钱”时,工人们无一例外地摇头,他们的工作就如同盲人摸象,有的人工作好几年,连最后成品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不用说手下做出产品的价值了。
第五天:娱乐赢钱了我请你去爽歪歪
到了晚上,工厂附近到处都是音乐开得超大声的溜冰城,招牌灯足有两人高的网吧,还有大大小小的烧烤摊,各地特色的大排挡,与白天的寂静形成鲜明的对比。泡网吧、唱K、溜冰,这是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打工生活的三大娱乐项目。大多数工厂都是24小时不间断开工,因此,同样24小时营业的网吧最受欢迎。聊QQ、玩网游最受追捧,不少网吧也实现“差异化经营”,部分电脑加强配置,专供网游,收费也高,部分电脑配置低收费低,供女孩子聊天用。
一位工友说,刚打工时,大家还会建立聊天群,同一个工厂的打工者相互交流。但后来渐渐失去了兴趣,几个月就换一份工作,此时前一个群的人都还没认全。这都属于比较健康的娱乐。工友中有一位负债累累的年轻人。从今年春节到现在,他已经输掉了4个月的工资近万元,还欠下4千多元债务。工厂里赌&博人群不在少数,下了班就开始,风雨无阻,没有休息日。这位工友说,上班实在太无聊,但只要想到晚上能“赌几把玩玩”,就觉得有动力,也觉得日子过得有意思。
相比之下,另外一种娱乐更刺激:买地下六&合&彩,每周开三期,买中了能获得40倍的回报赢利。“赢钱了我请你去爽歪歪”,这是工友们最喜欢的承诺,爽歪歪是附近一家娱乐城,可以溜冰、可以唱歌,还有很贵的按&摩服务。同生产线的一位工友说,他打工期间的梦想,就是每周能去一次爽歪歪。娱乐结束,回到宿舍又是另外一种生活。一个宿舍8个人,分属不同生产线,甚至不同部门,上班时间根本凑不到一块,我下班时,其他人有的赶着上夜班,有的在外面吃饭。有很多入厂几个月的工友,和宿舍其他人仍不认识,顶多下班时打声招呼,“回来了”。彼此间的关系,就像紧锁的柜门一样,正常而又有着距离。
第六天:消夜三成新民工5天花光工资
玩具厂的工友们年纪都比我小,无一例外都是“85后”。工作几天后,我和其中一两个渐渐熟悉,通过他们又约了几位工友,还有隔壁一个工厂厂长,大家一起消夜聊天。一位河南漯河的小伙子说,他已经在东莞呆了五年,其实心里早已厌倦,但回去没有更好的门路,不知道能干什么。谈起“梦想”时,工友们都会有点不屑,有吃有喝过日子,什么梦想不梦想的。对于他们而言,出路比梦想更为实际。
厂长姓冯,湖南衡阳人,从2005年到现在一直在虎门形形色色的工厂打工,从普工做到了厂长,工资也从每月几百元一路涨到了现在的5000元。在很多年轻人眼里,冯厂从最基层的工人做到了管理层,尽管还是一个打工仔,但他已经是“成功的代表”。几杯啤酒下肚,冯厂拍着我的肩膀说,不要问这些兄弟打工累不累,苦不苦。“每年的8月底,你到汽车站去看看,家长送小孩回家,小孩在车上哭,父母在地下哭,看到这一切你就都会明白”。
打工生活,除了累、枯燥,对于很多人来说更多是无奈,就如冯厂。冯厂感叹地说,以前为一个组长、一个主任,大家都要争破脑袋,但现在的年轻人,很少会为了这样的职位而去争、去抢,“大家都发扬风格,让给别人”。做个组长多几百块钱工资,却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几乎等于零。
“有时他们请我去唱歌,我都不好意思去”,冯厂说,他曾做过一个调查,发工资后的五天内,厂里有1/3的年轻人会把钱花得精光,然后找他预支下个月的工资。记者打工期间,就“打工工资是否要寄回家”这一问题,记者一共向56位“90后”找工者咨询,只有5位年轻人表示,如果家里有需要,开口向自己要,才会寄回去,其余51位均表示,家里不会找自己要钱,因为工资还不够自己花。
第七天:辞工“农二代”生活以城市为参照
新生代农民工,其实远不是一个“农民工”的词所能概括。与其父辈相比,他们从小到大衣食无忧,缺乏吃苦耐劳的品性,崇尚个性张扬,追求个人享受和社会尊严。“农一代”是以家乡为参照物,“农二代”却是以城市为参照物。
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着更强的认同感,但现实往往更残酷。
7月17日,我决定结束我的东莞打工体验,辞工返回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