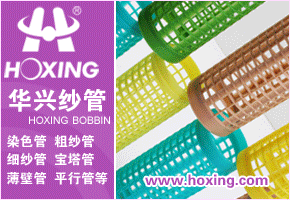从当代纺织女工的命运说起
不知从何时起,女人便成了上海这座城市霸气十足的主人。她们在忠实或稍打折扣地屡行传统相夫教子的职责之际,常常反客为主,反阴为阳,且驭夫有术,将不可一世的男子汉大丈夫调教得服服帖帖,俯首听命——这堪称为上海女人创造的一大奇迹。它已成了这座阴柔气十足的城市的鲜明标记。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多年前曾刻薄地讥讽过上海男人的软弱胆小,曾使当地不少男士羞愤交加,纷纷起而反驳。但平心而论,男与女,阳与阴,刚强与柔顺,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极,它们间存在着微妙的依存、勾连与转换。古代哲人老子早就窥测到了其中的奥秘,“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流水貌似柔顺平和,但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冲蚀刷洗,最终水滴石穿,最坚硬的石块也被蚀化得千姿百态,形成蔚为壮观的奇景。而原本如水般柔顺的女人,在社会性别与等级结构中处于弱势,但她们中的不少人,变被动为主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其中的佼佼者,不仅得心应手地辗转于厅堂与厨房,而且以莫大的勇气走入外部大千世界,创出一片天地,此刻,她们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女中豪杰。程小莹的新作《女红》中着力刻画的主人公秦海花,便是这样不平凡的女性。
小说书名“女红”原指女性所作的纺绩、刺绣、缝纫等事,但它和王安忆的《天香》不同,聚集点不在于上海明清时期刺绣工艺的演化,而是当代纺织女工的命运。每每提及上海,这些年人们听烦了喋喋不休的絮叨,它们如嗡嗡咿咿的飞虫,在空中久久盘桓徜徉。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刮起的怀旧风潮中,林林总总的文本倾心追慕、怀恋的是业已消散的繁华梦,它曾在上世纪20、30年代昙花一现,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构成了背景,衣着华贵的名士淑女进进出出,成为那一年代人们仰望的标杆。但这一半殖民地的繁华胜景并没有坚实的地基,很快便在战乱与革命的潮流中烟消云散。细细辨析之下不难发现,上海怀旧风吹拂的只是上海都市生活的一小爿,它在凸现中上层人士令人羡慕的西化生活方式的同时,遮蔽了对其他社会阶层的关注。作为中国现代工业的发源地,上海其实并不是一座优雅的城市,它在演变为现代超级大都市的过程中充满了血腥与暴力,其城市肌理从底子上说非常粗粝毛糙:它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五卅运动、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历史事件给它的城市记忆涂抹上了鲜红的印记。一百多年来,产业工人始终是城市居民中不可或缺的一支。与那些专注展示家短里长、姑嫂勃谿的都市作品文本不同,《女红》描写的是纺织女工及其她们的亲友,它将他们置于时代变革的漩涡中,细腻地勾画了他们因改革下岗而一度陷入困窘艰蹇,最终自强不息,在绝境中开拓就业新路的曲折生活历程。
在当代文学史上,对于工人阶层的书写人们并不陌生。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工人已不是一个简单的阶层称谓,而是承载了沉重的意识形态内涵,被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领头羊,他们的日常生活也被镀上了一层神圣的光晕。在当年名噪一时的《上海的早晨》中出现的工人形象,几乎无一不带有这一特性,他们已不再是真实鲜活的人物,而沦为了宏大历史叙事中的零部件。到了《女红》中,先前意识形态的油彩剥落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工人生活的真实呈现与还原,尽管在某些人眼里,不少描写有着美化之嫌。与昔日的宏大叙事相比,虽然读者也能从字里行间或多或少触摸到时代风云的变幻,但它们只是一些微型的小叙事,其重心是秦海花一家的悲欢哀乐和命运遭际。全书开首,秦海花正从人生的峰巅跌落下来:凭借着她的才干,她修成正果,成了这座大型纺织厂的厂长。但好景不长,国有企业关停并转的风潮猝然而至,人们面临关厂下岗的窘境。在此巨大的挑战面前,秦海花毅然带头下岗,与同伴们同命运共患难。几经波折,她搭准市场脉络,自立自强,创办了“布房间”集团,吸纳了大量下岗工友,从事方兴未艾的朝阳产业——养老服务,重新找回了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
平心而论,《女红》不是一部以情节见长的小说。除了秦海花外,她的丈夫高天宝,父母秦发奋、吴彩球,妹妹秦海草与前夫马跃,小炉匠,与秦海花相熟的男子李名扬、薛晖,他们构缀成了一个庞大的人物群。作者采取散点透视的手法,秦海花是其叙事链条的中心,但周围这些人并不是她的陪衬,他们有独立的生活与情感天地。正是通过似散实联的手法,数十年来上海的日常生活如一条汩汩奔流的河,涌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似乎又一次逆流而上,回到了昔日的年代,能够大口贪婪地嗅吸着那独特的气味,浸渍在较今日远为朴素的光影色调之中,任那些耳熟能详、甚至带有色情意味的方言切口在耳畔飘浮,体味到一种业已消逝的温情。
按照世俗的标准,秦海花等人都无从贴上“成功人士”的标签。但在她的身上,上海女性的勇气、才干、智慧、忠诚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然而,她这个女强人、女汉子又一点不缺少女人的魅力,不是超尘脱俗的圣女,她年轻时与李名扬曾有过若明若暗的暧昧、纠葛。在她身上,柔顺与坚硬,温情与决绝奇妙地融合成了一体,守雌而终为天下溪,成就了令其他女人羡慕不已的成就。
- 人大代表呼吁允许纺织等高强度行业女工提前退休 (03-10 08:32)
- 纺织女工1年在车间走1.2万公里 20年坚持三班倒 (12-29 08:49)
- 与纺织女工有关的两种记忆 (09-29 08:26)
- 东海农民变身纺织女工 (07-23 08:12)
- 一个纺织女工的无悔青春 (06-20 08:08)
- 纺织女工人大代表:“对于延迟退休,我们心存恐惧” (03-10 08:25)
- 两会访谈:新疆纺织女工的“蜕变人生” (03-10 08:23)
- 纺织女工,纺织工业部长之女 (10-31 0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