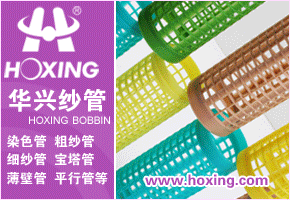好时光已经过去了吗? 中国制造遭遇困境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科技改变我们生活的最活生生的例子。这种改变当然没有因为郭先生发明了自己的散热方案而停止。从那时候开始,10年之后,世界再次发生了变化。
在昆山的厂房里,产品的加工和检测都是在高温中进行,年轻的工人在呼呼作响的大电扇旁,用娴熟而机械的动作,不停地产出各种规格的铜管。在不远处装有空调的车间,进门必须换鞋或者穿上鞋套,显示出精细加工对环境的需求——在这里,铜管被加工成形状各异的散热模组。经过最后的质量检验,它们被装进印有DELL或者HP字样的纸箱。叉车再次出动,将它们装入集装箱。集卡将从淀山湖镇出发,开上高速公路,根据距离的远近,若干天后,昆山、厦门、印度、东欧和南美的客户,将依次接到从这里发出的散热模组。它们随后被装进笔记本电脑中。货船再次起航,轻巧便携的笔记本电脑被运往包括中国在内的电器卖场,进入我们的生活。
据说,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是在一台HP电脑上,写出《世界是平的》这本著名的讨论全球化的畅销书的。弗里德曼先生的HP电脑里,是否也有一块产自中国淀山湖镇的散热模组呢?
笔记本电脑改变世界的方式不在于催生少数了不起的思想成果,而是以庞大的数量改变普通人的生活方式。这些年来 ,《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致力于一项让每个孩子拥有一部笔记本电脑的计划OLPC(OneLaptopPer Child)。他联合英特尔、谷歌和AMD这些IT巨头,极力降低笔记本电脑和软件的价格,再通过慈善机构的采购,将这些笔记本电脑送到贫穷的和缺乏教育机会的孩子手上。尼洛葛庞帝将笔记本电脑看作随身可以携带的人类智慧,认为它们将改变穷孩子的人生,进而改变这个世界。在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里,数量和低成本无疑是改变世界的关键所在——这正是郭先生和“中国制造”最擅长的领域。
但到了2008年,擅长降低成本的郭先生觉得,最好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郭先生想念一个模组价值10美元的黄金时代。好光景持续的时间不长,从2000年开始,到2002年结束,头尾不过3年时间。那时候郭先生的企业没有占到现在这么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净利润率在20%以上。
现在,25%的市场占有率并不能让他纾解愁眉。从2006年开始,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在蚕食他的利润。最先是原材料涨价。国际市场上,铜的价格从5年前就开始上升。有人说这是中国的大宗采购引起的。事实上,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对铜的需求都在上升。无论是中国和印度,还是“金砖四国”里的俄罗斯和巴西,经济的快速增长对电力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铜是制造电缆的主要材料。
到2008年,铜价已经翻了一倍。作为制作电脑散热模组的主要材料,铜价已经占到了到产品售价的80%。尽管如此,郭先生没有因此向客户提出涨价的要求,恰恰相反,因为笔记本电脑的普及和价格迅速下降,散热模组的价格还在下滑。
从2006年人民币放弃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之后,进入了一个时快时慢的对美元升值的通道,至今对美元一共升值20%左右。对于以美元结算产品价格而以人民币结算生产成本的出口企业来说,以廉价著称的“中国制造”的终端产品几乎没有涨价的空间,所以升值就意味着利润下降。
另一个打击是政府取消了对出口加工企业的税收优惠,作为台资出口企业,郭先生的感受十分典型。他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率从两税合并之前的最低12%上升到了25%,而增值税退税率从原来的17%降到了13%。
与此同时,由于激烈的竞争,欧美市场上的“中国制造”,价格已经压到了可能范围内的最低。
10余年前,郭先生的第一个客户DELL请他设计散热模组时,设计费100万元新台币,今天他的客户不需要另行支付任何设计费用。作为全球出货量第二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和郭先生最大的客户,DELL在亚洲、欧洲和南美洲都拥有自己的组装厂,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供货商向组装厂供货的时候,必须要自行负责物流和仓储。为此,郭先生必须在每一个 DELL组装厂旁边租赁仓库,储存自己的产品,供DELL提货所需。DELL由此保证了生产流程的零库存,巩固了自己的竞争力,而郭先生每个月需要支付200万元以上的仓储费用。
这种情形之所以会出现,唯一原因是市场已经供大于求。每个供货商都在想方设法降低成本,以获得欧美客户的青睐。廉价策略使得供货商们在和拥有终端产品品牌的客户谈判时,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这是一个糟糕的循环。
这个行业还没有糟糕到纺织业的地步:增值税退税已经成了许多出口纺织企业利润的全部来源。但盈利能力已经脆弱到企业对任何形式的成本增加都极度敏感。降低成本就是生存下去的唯一法则。
成本紧箍咒
有证据表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并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抱怨,但它们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感。在生产有淡季和旺季之分的出口制造企业里,加班本来是旺季的常态。昆山的最低月工资是850元,旺季工人的加班费可以达到基本工资的60%,是他们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劳动合同法》规定,每个工人每月加班时间不能超过32个小时。这几乎完全打破了制造业原有的生产节奏。到底有多少家企业真正是按照这个规定来做的就大可怀疑了。企业和工人往往会达成一种默契,他们装作不知道有这种规定。当然,一旦工人觉得这种做法不妥而向劳动局举报,企业就面临着非常麻烦的局面。
这种麻烦同样也是属于地方政府的。这些政府了解企业的需求,也很难真正下定决心去处置普遍存在的非法加班现象,但也不可能罔顾法律和举报。他们最后采用的方法是不停地向上级请示,希望得到更高层政府的明确处理意见,相似请示一层层上移,处理复杂局面的压力也随之上移。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每个国家都要在劳工权益和企业活力之间做出平衡,在中国,这是最高级别的议题。
因为“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就是来自于低成本——包括廉价的土地、人民币、能源和劳动力。长期以来,向成本要利润已经成了出口制造企业的中心诉求。
企业成长和一个国家的发展一样,有路径依赖。
在廉价倾销的策略里,成本是永远的紧箍咒。制造业资本像穿上了有魔力的舞鞋,永远不能停止寻找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脚步。
在台湾,郭先生的父亲,一位多年前从江西吉安到台湾去的老人是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的忠实观众。电视新闻里大陆经济欣欣向荣,每每惹动老人的思乡之情。但作为台商的郭先生,心情要比用乡愁过滤新闻的老父复杂得多。
10年前,为了降低成本,郭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念叨着“大陆”的字眼,从台北来到昆山;10年后,他的朋友和同行们见面时,嘴里念叨的热门词儿,已经从“大陆”变成“越南”了。
寻找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过程,不是从今天、也不是从中国制造开始的。
寻找成本洼地
出租车从东莞市区驶往和深圳比邻的塘厦镇,高速公路覆盖着茂密的热带植物,而两旁除了闪过香蕉累累的果园,还有随处可见的厂房和职工宿舍。职工宿舍的阳台上晾晒着颜色和式样都相同的服装,告诉我们,这里正是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中心,是“台湾制造”和“香港制造”落户内地的第一站。
塘厦镇的一个角落里坐落着一家员工达到3000人的五金制造企业,在工厂的产品陈列间里,我们看到了和昆山的郭先生生产的一模一样的产品。这两家工厂相距数千公里,分属两个行业,规模迥异,昆山的电子工厂隶属于一家台湾上市公司,而东莞的五金工厂是一家家族企业。但这两家看上去八杆子打不到的工厂,其实都是台湾的吴家三兄弟创办的。
吴氏的家族企业起家于1970年代,最初只是一个制作小五金件的家庭作坊。战后日本经济起飞,纺织、五金这样的行业迅速在成本的挤压下逃离日本本土,涌入前殖民地台湾,台湾岛内的五金加工厂加班加点也来不及应付所有的订单,最终采取的办法和现在东莞的五金厂毫无二致,一些订单因此从大厂流入到小规模的家庭作坊。
在许多年时间里,流到吴家作坊里的单子是铝制品加工:为日本产的高档音响的铝制外壳做表面处理,兼做铝质的真空管散热器。
这些不起眼的外贸代工单子不仅养活了吴氏三兄弟的家庭,而且使他们的作坊变成了现代工厂,并且有机会在30年后的议论产业升级的大潮中,再次从家族所有的五金制造企业变身为主营IT产品的上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