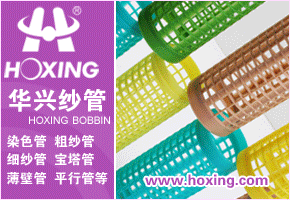“中国制造”真实困境
海洲服饰董事长李林锋曾经有类似的痛苦经历。去年春节的前两天,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打电话催债,即使春节过后,还有60万欧元的货款无法到位,而这些货款还是前年亲戚朋友们欠下的。“一年比一年艰难。”温州丑鸭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潘跃说。在过去的几个月,他的公司只有一半的货款到。他坦言,“明年可能一半的应收款都不能到位,而且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 。
“破产之城”?
在成本和价格出现往相反方向变化的时候,等待实力稍弱企业的命运,或许只有关闭这一条路。对于现在多数温州商人而言,转业破产似乎早已司空见惯了。这个宝马汽车数量占据全国1/4、中华香烟每年抽掉7亿的聚金之地,似乎正从“老板之城”变成“破产之城”。
温州龙湾工业园区,与夜市疯狂倾销的场面相比,白天这里反倒冷清很多,下午不到五点就草草收工了。这里的鞋厂通常计件发放工资,一双30美元的鞋子他们可以赚到五角钱。在弥散着化学胶水味道的制鞋车间里,那些熟练的女工平均每月的工资可高达两三千元,而且劳动环境宽松了很多——他们只要干完手头分配的活,就可以随时下班,工厂也不要求加班。而在去年八九月份,他们身后的鞋子还一直堆到天花板上。这里有“中国鞋都”之称,超过60%用于出口,但平均单价通常只有不到5美元。
无疑,洗牌正在不知不觉中加剧。5年前这里有超过5000家鞋厂,而现在只有不到一半活了下来。而根据温州市鞋革行业协会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第一个季度中,倒闭转产的制鞋企业超过了70家,那些存活下来的工厂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留住人——在龙湾工业区内,不少鞋厂门口的牌子上都用红笔写着招聘启事,吸引工人的条件五花八门,比如提供夫妻房、住房补贴、提供自行做饭的场所、如果亲戚都在工厂工资,则推荐者可以得到数百元不等的奖励。
在离龙湾工业园区不远的温州技术开发区内,企业猝死的事件同样时有发生。最极端的案例是,去年10月初,温州华杉服装厂的工人们被通知开紧急会议,声称要突击检查需要歇业整顿3天。3天之后,人们发现这家工厂设备以及物料都奇迹般蒸发了。这家公司的老板吴理勇、吴理武兄弟不见去向。愤怒的工人一度阻塞了当地政府门前的道路——老板甚至将工资以及进厂押金都席卷一空。时光倒退到半年前,吴氏兄弟还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刚过不惑之年的吴氏兄弟以家庭作坊起家,2007年之前一直在乐清市磐石镇开办服装厂,在这里一步步站稳脚跟。为了扩大规模,吴决定转战温州,而华杉则是其并购的温州当地一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服装企业,拥有厂房面积多达数万平方米,一度拥有员工1200人。
类似的恶性逃匿事件,绝非仅此一例。今年开春时节到5月,是服装贸易型企业公认的淡季。根据温州市经贸委的调查,2007年底,仅乐清和温州开发区就有6家企业因资金链问题而倒闭,涉及的资金高达4亿多元。事发之后,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则不得不实行“清欠工资”职能,进行了全面排查工资发放情况的整治活动。“很多企业都因为相互拆借和三角债很难熬下去。”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对《环球企业家》说。
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的趋势悄悄出现,很多利润微薄的企业铤而走险进行地下融资,以缓解资金困难。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企业眼中,温州民间金融正从“地摊”形态正逐步登堂入室,企业家对之爱恨交加。“民间私下拆借的兴起反映微利时代企业家的无奈。”周说。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涉及民间借贷利率的监测数据表明,这一偏保守的官方数据表明,1月份温州民间借贷月息达到创纪录的11.77‰。“温州民间借贷大部分依靠人际关系,一般只打个借条,借条上甚至连资金借出方的姓名都没有,利率多是只有口头协商或随行就市。甚至有一批专门的金融掮客以此为业。”浙江金克明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合敬说。
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则是在温州几乎少有破产的官司接手。“如果你做破产方面的律师,那就等于饿死。”林认为温州尽管催生了强大的市场经济,但产权和法律意识依然淡漠。温州人可以了无声息地关门,但并不习惯严格意义上的企业破产注销,“他们的契约通常只写在一个巴掌大的纸上,有时候连一片纸都没有”。
破局和重生
或许让外界感到欣慰的是,温州并不担心被外界遗忘,这个城市每天都有无数企业破产,也有无数企业绝处逢生。